出国之前就听说过出国的人会经历“文化休克”(culture shock)。所谓“文化休克”这个概念,是指由于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社会交往信号或符号,对于对方的社会符号不熟悉,而在心理上产生的深度焦虑症,出现迷失、疑惑、排斥甚至恐惧的感觉。当一个长期适应于自己母国文化的人到另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中时,其常常会在一段时间内出现这种文化休克现象。
对于文化休克,我曾不以为然。上初中的时候我便偏爱英语,英语科代表一直当到初中毕业。但那时对英文的喜爱只是好奇心所致,等到后来渐渐懂事,就把英语当做一种工具去了解欧美文化,就好像英语是个高倍数的望远镜,用它可以看到遥远的另外一个世界。
九年前临来加拿大之前,国内的互联网并没有象现在这样发达与普及。但因为看过许多外国电影,读过一些英文书与文章,便感觉自己象打过预防针一样,到了加拿大断然不会因为文化差异而休克过去,甚至连洋人跟老婆见面或道别贴脸都做好了思想准备。
当初,让我担心的是到了加拿大我的中国文化会不会失血过多,我可是自幼便喜爱诗词歌赋,长大后更因为深信“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”,所以爱书如命,中华文化已深植于我内心深处,溶于我骨血之中了。
我经历的异国文化
来加拿大之后,先在魁北克城和蒙特利尔附近的dorval待了两年。那儿的中国人特少,人在异国他乡的感觉也特别强烈,就如踏着彩虹走进海市蜃楼一样,一切都有不真实的感觉。
儿子来的时候刚满四岁,他去的那个幼儿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小孩。那是魁北克城一个非常好的幼儿园,儿子的到来迅即成为那个幼儿园的爆炸性新闻,每个小孩的家长都知道来了一个中国男孩,以至于隆重到幼儿园还在儿子入园的那一天办了个中国日。墙上挂满了跟中国有关的画,老师专门为孩子们讲中国的长城,中国的历史,中国的大熊猫……
而儿子那时也长得特别可爱,受到了大熊猫一样的待遇,尤其是小女孩特别喜欢他。每次我送他,总能看见有小女孩抢着或拉他的手,或拥抱他,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。而每次接他,总有小女孩送他各式各样的礼物,并且写着“我爱你,lee”。
有一次我去得稍稍早一点,看见我儿子在饮水机那喝水,而他身后有一个小女孩正在深情地抚摸着他的头发。我不禁对那一幕非常感动并有些shocked,我知道法国人浪漫,但是一个四岁的小女孩能有如此的浪漫和爱心却让我有些shocked。
魁北克人善良热情,民风古朴。我们刚去时还没有车,去超市购物回来的时候,如果手上拿的东西多,经常会有人停下车来问你需不需要帮忙。
妻子那时在laval大学学习,laval大学有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和学者。我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来自比利时的tom帮我介绍的,而另一个比利时的博士pirrie曾经每一个星期天无偿地教我学开车,而且是手动车,直到我学会考到驾照为止。
我到现在还记得第一次跟pirrie开上高速公路,开过宏伟壮观的魁北克st. lawrance河大桥,似乎我的心也在飞一样。
那时会有人关心地问我有没有“culture shock”,我都会象当地人一样耸一耸肩,把手一摊,轻松地说“ no”。
我在异国经历的中国文化
有一次去美国路过多伦多,那是妻子第一次到多伦多。我们在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饭,席间老板送了两碗栗子面做的粥,这栗子面做的粥竟勾起妻子无尽的乡思,想不到多伦多还有如此正宗的中国食品。
我对吃的倒是从不挑剔,可妻子却跟我不一样,她是头脑可以适应这里的文化,但胃口却只对中国饮食忠贞不二的人。我见她动了思乡之情,便坚定地安慰她:“我们搬到多伦多来,让我们在多伦多开创我们在加拿大的未来。”
后来,我们还就真的搬到了多伦多。到了多伦多才知道为什么多元文化是加拿大的基本国策。不管你来自世界上任何角落,你都可以在多伦多找到家的感觉。culture shock变成了multi-culture shock,而且给我shock最深的恰恰是这里的中国文化。
有一次我们去sears家具店买side table,走过来一位儒雅的先生,他用台湾电视剧里的“国语”腔问我们: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?”我们告诉他我们要买side table,他便带我们看遍了店里的side table,可都不是我们想要的那种。他又到电脑里帮我们查,也没有查到。虽然没有买到我们想要买的,可我们对他的服务特别满意,我发自内心地对他说:“谢谢你!”
他连连对我说,“哪里,哪里”。他的一句“哪里,哪里”不禁让我感慨万千,就好像在他乡重逢了久违了的知音一样。在时髦的现在,很少有人说“哪里,哪里”了,只有上了一些年纪受过传统的中文教育的人才会说“哪里,哪里”。想不到在加拿大还能听到这样正宗的中华礼仪之语。
其实语言只是表面,语言的灵魂是文化。他的一句“哪里,哪里”让我想起一则笑话:早年的时候,有一中国官员携夫人访问美国,美国的官员带着美国的翻译到机场迎接。中国官员和夫人下了飞机后,美国官员上前问候,美国官员说:“夫人很漂亮!”中国官员说:“哪里,哪里。”因为美国翻译不懂中国文化,便直译成“where? where?”结果让美国官员大吃一惊,不知所措,只好说:“everywhere!”
多伦多北面有一小镇叫dorset。dorset是赏枫的好去处,湖光山色,小桥流水,登上高塔之顶,放眼望去,层林尽染,万山红遍,让人陶醉。我在dorset还有另外一个发现,那就是赏枫的人中,百分之八十甚至百分之九十都是中国人。这一定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影响,赏枫赏月从来都 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到dorset赏枫的中国人,即使是身在异国,但触景生情,想到也一定是中国的古诗: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
中国的古诗不但影响着华人,也影响着西方世界。有一次我在多伦多公车局(ttc)的地铁里看到了翻译成英文的李商隐的诗:“君问归期未有期,巴山夜雨涨秋池,何当共剪西窗烛,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细细读着译成英文的诗,虽然怎么也读不出中文原诗那种韵律感和意境,但已足够让我自豪了。想不到在诗人在中国快要绝迹的时代,我竟能在异国他乡的多伦多地铁里用英文读到我最喜欢的那首唐诗。
以前在魁北克,中国饭店不多。即便是仅有的那几家,做出的也是加拿大式的中国菜,十分的不地道。而在多伦多,中国各大菜系的中国餐馆均是原汁原味。不仅如此,有的饭店竟然有原国宴御用厨师掌勺,在多伦多一著名的食轩,我们品尝到了在国内也未曾吃过的宫廷御宴。还有一家东北饭店,不但东北菜做的地道,环境也很中国,天棚上挂着两条长龙的风筝,墙上是中国结,中国玉,或是中国的工艺品。据说老板娘还是京剧名旦,她端盘上菜,喊着菜名的时候,我总幻想成她挥着长袖,扮着旦装,在舞台上亦歌亦舞的美丽画面。
在多伦多我们还有幸接触到了几位中国文化名人。我们在多伦多结识的一个好朋友的父母是国内著名的陶艺艺术家,他们曾经世界各地讲学办展览,而且他们的作品曾被美国总统收藏。后来他们到多伦多的女儿家探亲,住了一年多。
每个星期六的上午,儿子去中文学校学中文,为了鼓励他,我每个星期六都带他去麦当劳吃早饭,他最喜欢麦当劳的hashbrowns。一次,一个风度翩翩的人听我们讲北方话,便主动跟我们打招呼。这人一看就是个艺术家,尤其说话时嗓音富有磁性,不同凡响。
后来我们经常在那家麦当劳碰到他,跟他在一张桌子吃早饭,才知道了他就是大名鼎鼎的歌唱家李小护。只恨我见识短浅,当时是有眼不识泰山,没有主动跟他打招呼。后来终于在中央电视台“同一首歌”走进加拿大的晚会上见识到了他大师级的功底。
真正的文化休克
自我们搬到多伦多以后,儿子就再也没有在魁北克的那种待遇了。他在多伦多上的小学里一半多是中国孩子。我想这样也好,我要利用多伦多的multi-culture的优势让他学好中文,我便每个周末把他送到多伦多教育局办的中文学校去学中文。
儿子去了中文学校没几次,有一天回家便自豪地告诉我他会写中国字了。我急忙问他会写哪个字,他说是爷爷的“爷”字。我立刻拿出笔和纸来让他写,只见他上面写一个英文字母“x”,下面写一个英文字母“p”,告诉我这就是“爷”字。
看着他用英文字母x和p组合而成的汉字“爷”字,竟让我哭笑不得,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他问我:“爸爸你怎么了?”
我说:“儿子,你让爸爸第一次有了culture shock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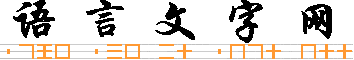




 请相信我我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同胞们这也是我在欧洲的生活经验:让孩子在课余来本站认识、欣赏一些甲骨文,也可以去象形字典网站(vividic.com)查看更多甲骨文字体,还有很多字源视频、文章,这样孩子学习汉语就有更大兴趣且不会写错字了。这比查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〉还有效!同时,父母必须造就跟孩子一直说母语的语境,这样孩子长大了,汉语交流至少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。生活在英语国家当然不必对孩子的英语有任何担忧,因为周围都是英语语境,且孩子几乎都是语言的天才!孩子在德国、奥地利则通德语,在法国长大则通法语,在意大利则通意大利语,在魁北克则法语、英语都会弄通的;在北美长大成为英语通也是家常便饭、水到渠成的事儿。母语是我们的根,把根留住!哈哈。
请相信我我这绝对不是开玩笑啊同胞们这也是我在欧洲的生活经验:让孩子在课余来本站认识、欣赏一些甲骨文,也可以去象形字典网站(vividic.com)查看更多甲骨文字体,还有很多字源视频、文章,这样孩子学习汉语就有更大兴趣且不会写错字了。这比查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〉还有效!同时,父母必须造就跟孩子一直说母语的语境,这样孩子长大了,汉语交流至少就不会有什么大问题了。生活在英语国家当然不必对孩子的英语有任何担忧,因为周围都是英语语境,且孩子几乎都是语言的天才!孩子在德国、奥地利则通德语,在法国长大则通法语,在意大利则通意大利语,在魁北克则法语、英语都会弄通的;在北美长大成为英语通也是家常便饭、水到渠成的事儿。母语是我们的根,把根留住!哈哈。